.txt成人av片无码免费天天看
最佳回答
“成人av片无码免费天天看”.txt成人av片无码免费天天看
中国新闻周刊记者:徐鹏远
发于2026.1.5总第1219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 刘擎: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
刘擎: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
影响力学者
他的名字响彻学界,被同行称为“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存在”。他从事着小众的学问研究,却破圈成为大众心中的宝藏导师。他是思想的摆渡人,努力以深厚的学养与非凡的洞察,将学术、智识引导至公共生活的岸边。他的公共发言,在纷繁的舆论中为大众重建理性的坐标。他让我们相信,学术并非悬浮的概念,学者也不只会囿于书斋。他审慎而清晰,温和又锐利,始终守护着思想的灯火与尊严。
2025年岁末,刘擎去了一趟南极。
这是他迄今行程最长的旅行,仅从上海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就飞了30个小时,而后还要取道火地岛的小城乌斯怀亚,再搭乘游轮跨越德雷克海峡。迂途迢递,一路辗转,体力和精力都备受挑战。然而当慵懒的海豹、憨萌的企鹅、翻腾的鲸鱼和无垠的茫茫冰原映入眼帘,所有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了。“只觉得一切都很值得,这是你第一次面对绝对自然的景观,而且是一个如此巨大的存在。”他说。
在南极,刘擎度过了“与世隔绝”的九天。这是一段难得的偷闲时光,自从几年前因为《奇葩说》破圈走红,忙碌成了他的生活常态。他好像突然之间被所有人需要,各种邀约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来。
对此,他起初有些恐慌,担心被这条轨道绑架,变得面目全非,也害怕说得多了难免重复,令人生厌。不过现在他想通了,无论深居学院还是跃入公共舆论场,自己其实都是一个教师,这是他喜欢的,亦是他擅长的。
“我可能做得最好的(角色)就是教师。我不纠结自己是不是能够成为多么优秀的学者,即使我愿意,也做不了学术巨人。对个人来说,我在公共领域里获得的心流体验和愉悦感、成就感可能更强,它让我开阔了很多眼界,打破了很多边界。”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人文主义烙印
动身去南极之前,刘擎刚刚上线了自己新做的播客。在“发刊词”中,他称其为一档从失眠开始的节目,所以取名“夜思”,意为“夜游者的思绪”。
从年轻时起,刘擎就是一个夜猫子,习惯于凌晨五点才入眠,他经常猜想也许祖辈做过守夜人,自己继承了晚睡的基因。独自清醒的时候,精神总是活跃异常,思绪如翻江倒海,有些一闪而过,有些则蛮有意思,不妨讲出来跟人聊聊,算是思想的草稿,没准能为日后成形的表达提供一个基础。
既是草稿,不免散漫,但零零碎碎之间却也草蛇灰线地串联着隐微的脉络——那是一份对于人文主义的执守,一种有关共同命运的忧虑。
对刘擎而言,人文主义是一个稳固的立场。特别是前两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时,他恍然意识到自己做过的许多事情看似驳杂,其实尽皆归于一个宗旨:在现代性的条件下重建人文主义。包括过去一年他主要思索的两个问题,一个关于新技术,一个关于爱情,同样是在这一方向上的掘进。
“我对新技术的关注,重点不在于它能够帮助人类实现什么,我更关心它对人性的改造。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,从古希腊哲学到后来的海德格尔、斯蒂格勒都强调技术不只是人类的工具,也参与塑造人性。我最近的发现是新一代技术不仅造成了理性思维的衰落,也瓦解着我们的感官能力。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么多‘淡人’‘I人’‘社恐’,就是由于过度投喂的代偿性刺激和满足钝化了天然的感受性。而当这种感官能力弱化,我们的情感会随之发生退化,不仅与家人、朋友、师生、同事、邻居的关系变得淡薄,亲密关系也出现了问题,爱情开始式微。”刘擎说。
在刘擎看来,种种这些都是一种征兆,映显着人文主义价值在当代情境下受到的冲击与挑战。为此8月份的时候,他还专门在“得到”制作了《爱情哲学30讲》,完整阐释自己的观察与读解。
人文主义的烙印,在刘擎身上由来已久。早在华东纺织工学院(今东华大学)读书期间,他便已迈出了追索的脚步,借由的路径是文学、戏剧:1985年,他和几个朋友成立了“白蝙蝠戏剧实验室”,理念就是通过戏剧“使人成为人”;1986年,剧社排演实验话剧《生存还是毁灭》,将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与社会新闻、时代信息相融合,对人性和现代文明展开讨论;1989年,他又创作了剧本《极乐游戏》,以“什么是存在”的究问为起点,写出一场“生命偷渡”科幻故事。
不过当初的他只是一名化工专业的学生,没有完备的知识体系打底,所有萌动大抵出于青春激情与书生意气,朦胧而虚浮。并且从根本上说,人文主义在彼时的整体环境中也缺乏足够充分的生长空间:“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,现代化是特别有感召力的,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反思现代性的维度,所谓三大思想流派——‘走向未来’‘中国文化书院’和‘文化:中国与世界’,包括尼采、韦伯、海德格尔、法兰克福学派等等资源,但是我们没有特别强的亲身感受。”
于是为了继续深入地探寻,刘擎决定出国留学。1991年,他远赴马凯特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,攻读政治学硕士、博士学位。逐渐地,他的意识开始愈发明确,思路也变得清晰起来。“在美国的九年,我形成了对现代性的立场,这个立场就是批判性的肯定。现代性带来了巨大的平等、自由和个人权利,它是一个desirable(可取)的成就,但它同时是有问题的。”由此,他也终于确立了属于自己的思想命题,即如何在一个被工具理性主导宰制的现代世界中恢复人与世界、人与人之间的本真关系。
“这是我所有努力的焦点,既让个人生命充盈着这种追求,也致力于让世界能有超越生物性的那一面。”刘擎说,有时候他甚至心生伤感,不确定人类会不会终有一天完全脱离这种价值理性,更不知道自己的坚守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作用,又或者原本就只是一种知识的傲慢和徒劳而已。
但在南极的日子,一道光似乎冲破了忧思的暗影。12月的南极,太阳终日不落,极昼的夜里,刘擎的思绪比平日更加泛滥。他看着眼前那片原始的纯净,百感交集,一份从未有过的宁静悄然间涌上心头。
“你会觉得人类何等渺小,进而你会用一个新的尺度来看待人文主义。它不过才两三百年的历史,只是人类文明、地球文明、宇宙文明的一个阶段,在这个意义上,你可以泰然接受它的任何命运。这不是说它的命运不值一提,而是世界就是这样流变的。”刘擎说。
介入的旁观者
从南极回来,刘擎的日程立马又变得拥挤起来。他只休息了一天,时差都还没有调整过来就要赶去长沙,录制最后一期《再见爱人》。
这是他2025年的全新跨界,也是《奇葩说》之后再一次登陆综艺。其实节目组几年前就发出过邀请,他一直觉得不适合自己,直到《爱情哲学30讲》上线:“很偶然地,有一次又遇到了节目的编导,他们说你现在不是正好在讲爱情哲学吗,可以把你的课程想法注入进去。这一点打动了我。”
然而真正参与下来,刘擎觉得这次尝试并不算成功。虽然过程之中也会与一些意外的喜悦不期而遇,但总体而言,自己的发挥和能够获得的接受度终究是局限的。
对于跨界的边界与风险,他一直是清醒的,破圈这几年,他拒绝过无数个MCN公司递来的合约,避免被流量所曲解、裹挟和吞噬。他甚至觉得,即便自己时刻怀揣反思与质疑的态度,还是可能部分地成为流行和商业的同谋,“就像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·布尔迪厄当年在电视上批判电视一样,构成一种反讽和悖论”。
这是一道永远充满考验与代价的题目,没有标准答案。“除非不去做,麻烦就都没有。但是如果不做就会更好吗?如果所有学者都把自己关起来,公共空间的质量会不会更差?如果世界全是污泥,我们真的能出污泥而不染吗?”因此尽管存有保留与警惕,面对通向公共的入口,他仍然选择躬身笃行。
在对自我的判断上,刘擎始终觉得,他是一个被高估的学者,自己真正做得比较好的是把思想资源跟现实问题放在一起做观照。“我在知识上有相对开阔的视野,这个特点作为一个学者并不能够完全用到,但作为一个大众的教师可能是有优势的。那么,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别人很难替代的工作,对我来说是成就更好的自己,对社会来说是发挥了最大价值。”
最初的刘擎就是一个舞台中心的人。他曾是20世纪80年代上海文化圈的一颗明星,左手写诗右手评论,最擅长的是演讲,临场发挥便能出口成章,并且极富感染力。彼时德高望重的文论家王元化等人都对他青睐有加。
只是后来,他从时代现场退出了,转身跃入一个沉静的学术世界。整个90年代,他都埋首于哲学的象牙塔,如同清教徒一般苦修。相识多年的老友许纪霖开过一个玩笑,说美国把他变成了乡下人,他也觉得从前的自己好像消失了,通身换了一副模样。
再次的转变始于千禧年代。2003年刘擎回国任教,一年以后,理查德·罗蒂来华访问,停留上海时,这位美国哲学家跟他讲了一句话:“哲学变得有一种increasing irrelevance(日益增长的无关紧要性)。”在那之前,他写了一篇《政治哲学的奇异沉寂》,谈论过这个专业与外部世界的分离,越来越成为“生产文本的文本”的学科,但罗蒂的话还是给了他很大的冲击。
“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,从柏拉图到霍布斯,从洛克到卢梭,所有人都特别关注自身的时代,他们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很近的。”他意识到倘若远离了社会和时代,最终是会导向某种枯竭的,“政治哲学是关于共同生活的”。
也是在这一年,他发表了一篇文章,对此前一年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进行回顾。本来这只是一次偶然的约稿,但他把它一直写了下去,连续写了十八年。在这份被学者陈嘉映称为“国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来”的思想观察上,他开始有意地为自己创造一个缝隙,既保持着对时代动态的关注,也努力于向公共领域输出。
2005年,他还把自己讲授的《二十世纪西方思想文化潮流》搬上了网络,尝试着让教室变得再大一些。等到知识付费时代到来,他又制作了一版全新的《西方现代思想讲义》。再后来,马东成为这门课的听众之一,并联系了他,提出合作的想法。
就这样,年轻时的刘擎一步一步地归来了。而且经历过岁月沉淀和智识训练,他更多了一份抽离的自觉,借用法国哲学家雷蒙·阿隆的一本书,他称之为“介入的旁观者”。
只是偶尔,他还是会有迟疑的瞬间。就在参加《奇葩说》时,有一次录制结束,他回去批阅一个博士的论文,从材料到行文,从论述到观点,看得出作者付出了不少心血。可越是如此,他越觉悲凉:学院里有很多人特别辛苦,做的工作却没被看见——“只有我们这样的人被看见了”。
低版本的伯林
如今的刘擎是许多人的知识偶像,而在哲学的巍巍殿堂里,他其实也有自己的偶像,尤其崇敬的首推韦伯与哈贝马斯。他向往成为像他们一样伟大的思想者,但同时知道自己就算终其一生也不可企及。
“我是一个兴趣特别广的人,像孩子一样好奇,很容易分心,性情上比较喜欢玩。我可能差不多是一个低版本的以赛亚·伯林,他是一个重要的知识分子,但又是一个被耽误的哲学家,他也太喜欢玩了,喜欢演讲,说的比写的多。”
曾经,刘擎为此失落过,沮丧和不甘于没有一个“扔在桌上砸个坑”的东西拿得出手。他本来有过这样的计划,好些年前就想要写一本专著,创造一个“广义政治学”的概念,打通从经典的国家政治、国际政治与世界政治到后现代的生命政治、身体政治和性别政治等之间的壁垒,构建一套融贯的理论框架。可惜直至现在,这本书都没能写出来。
不过已然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纪,他对此不再如往昔一般执着。他清楚,自己完成的能力与题目的野心之间存在着不易跨越的鸿沟,它来自天生的心性。倘若把学术比作建筑,他更像是一个设计师,喜欢构想,不喜欢施工,因为构想是兴奋的,施工是麻烦的。
“在这个意义上,我是一个过于随性的人,有点溺爱自己,放任自己享受,而无法成为一个原创性的理论生产者。”他说。
而且从许多青年学人身上,刘擎也感到一种释然:“年轻一代都起来了,学术很扎实,写的文章很漂亮,他们做的东西比你好,你根本不是不可替代的。”甚至他认为,某种意义上,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都走到了边缘:“未来的二三十年,新的技术条件和地缘政治的新格局,会让古今中西的问题有新的版本,所以我们这一代就过去了。(何况)对于公共生活的贡献,无论是伦理意义上、政治意义上、道德意义上、美学意义上,作为群像的我们完成得不算多好。”
当然那本“事先张扬”的专著,将来的某一天也许会再捡起,包括一些小说的构想或者重拾编剧之笔写几个剧本——“如果还有二十年寿命的话,可能都会尝试”。另一个学术的题目也一样,大概一年多前,刘擎脑子里一个长期的感觉突然有了清晰想法:“名字我都想好了,叫《‘病’就是‘坏’》。我们有两种语言来对待‘他—我’关系当中产生的问题,一类是道德的解释,另一类是病理学的解释。从近代科学开始,病理学解释越来越多地进入道德领域,最后会瓦解整个的道德论述框架。这很有意思,可以像福柯一样做一个道德谱系学的工作,考证它是怎么转变的。而且我预测,道德语言以后会被废弃,就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抛弃的神秘性巫术语言一样。”
哪个都说不准。活过了六十岁,外在的一切都没那么重要,从心所欲就好,哪怕明天就死掉,这一生也足够值得了。唯一惭愧的是,他觉得自己到底有些辜负命运的眷顾:“这个世界赠予我太多,我配不上我所收获的东西。”
声明:刊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稿件务经书面授权
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
- 评论
- 关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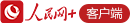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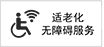

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
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
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
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
 关注人民网,传播正能量
关注人民网,传播正能量